这是个势利的社会,我深知,所以每天出门前先要想想去哪,然后再决定当天的穿着。要是到高档场所采风就要穿得尽量体面,以免遭白眼。到批发市场购物则要穿得朴素,省得招歹人惦记。
也许北京近十年形成了许多流行新天地,但亮马桥一带一直是我心目中北京最耀眼的时尚前沿。燕莎商城,长城饭店,昆仑饭店这个三角地曾经是富人的购物场。一位身着轻便装,等着门童来扛高尔夫球袋的妙龄少女格外显眼,使我不由联想起了当下的红人郭美美。燕莎的舶来品仍然是贵得乍舌。只要是进口商品,标价多高都有可能,也都会有人消费。这里从来就不是靠薄利多销取胜的,存在就有它的理由。商城里老外寥寥无几,殷实的国人才是真实的买主。即使在普通商场,如果按标价我用国外的工资购买也不轻松,如果是进口产品售价比国外还要贵许多。这使我回国购物优势全无。普通商店里也净是些三十岁往下的年轻人。我经常替父母抱怨:“这日子怎么过呀!”
北京好象很难见到北京人了。各行各业都让外地人包了。操着标准普通话的售货员服务完你转身就用家乡话与他们的同乡攀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普通话很像英语。不禁要问,北京人都哪去了?
民警不用出警了,工作包给了协警或协管,门卫的工作转给了保安,护士的工作转给了护工。一方面这些编制内北京籍人士不必亲力亲为,一方面又给外地寻工者创造工作机会,可谓一举两得,皆大欢喜。也解释了我先前的疑问。本地人很多因为拆迁用补偿款买了较偏远的住房,剩下的钱仍数目可观就留着养老了。很多人提前退了休,上班的也躲到了办公室指手划脚,一线的辛苦活都转给了外地工。
国家大剧院也去了,这也是我本次回国同长安街的唯一的一次亲密接触。150元人民币的戏票坐在近乎最后一排。上演的是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由陈佩斯等人将部分对白与时俱进地改编成了中文并掺杂了些搞笑情节。我不是戏剧专业人士,但觉得演员演技水平和布景还很不错。剧情则是一对西人夫妇各自偷情、寻欢作乐最后尴尬收场的荒诞剧。不知是演员的出色表演,还是迎合了现代国人不甘寂寞,追求生活丰富多彩的心理,掌声喝彩声经久不息。我也在认真思考这部剧的主题和导演希望向观众传达的信息。
我还特意走访了名扬海外的“唐家岭”——着名的北京蚁族聚集地。但可能因为此地名气太大,原来的村子已经被整体拆迁了,据说是政府志在改善这里的住房条件,要统一规划新建青年公寓。收入微薄的大学毕业生本来是冲着低房租来落户的,不知道有几人还会迁回来。我只能象征性地在周边看了看,这些位于城乡交界处的聚集地,往往是不愿离京的大学生和毕了业的外地学生到北京的临时安身之所,他们靠租当地人简陋的平房作为进京的第一步。这些距北京北五环仅二十公里外的大小聚集地,随处可见简陋的饭馆商店,臭气熏天的河沟和泥泞的马路,垃圾被随意倾倒在路边,与北京气宇轩昂的城市景观判若两个世界。年轻人不怕吃苦,他们期待着从这里起步成就明天的辉煌,这可能就是蚁族的精神。
在许多居民区,我都看到了提防网络诈骗或电话诈骗的宣传栏。里面描述的花招千奇百怪,有的冒充警察、检察院,有的自称来自邮局,有的则是以恭喜中奖来引诱,蜂麻燕雀, 不择手段。我和同学朋友在一起聚会时,也经常有没头没脑的电话打来,有介绍房产、股票、黄金投资的,有推销产品的, 有关于健康讲座的,真假难辨(我猜想很多打电话忽悠人的销售代表可能就来自我刚刚探访过的“蚁族”)。怪不得我从澳洲打电话给国内的亲友,许多人发现电话号码奇怪连接都懒得接或直接删除可疑的短信,一概当作骚扰电话处理。有的朋友父母接了我的电话,报了名姓后还左问右问,非常警惕,原来这一切都事出有因。人们对这个社会越来越缺乏信任了。在国内时,恰逢“七一”将至。电视,报纸和街头巷尾是铺天盖地的红海洋,红歌也不绝于耳。我不禁突发奇想,当前“全世界最低的牛奶标准与最红的社会之相互关系”倒是可以作为一个有趣的博士论题。
我自认为比别人更懂中国,这并不因为我从中国而来,更因为我现在置身中国之外。我还没变成“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老华侨就有这种久别故土的沧桑感,而且确实“儿童相见不相识”了。再加上连日来对地名的无知,流行语的混淆,潜规则的不谙,价值观的错乱,在餐桌上的不胜酒力和在公共场合不堪烟雾缭绕……我深深感叹这个城市和国家已经有了新一批的主人,自己就像那辆不肯和人扎堆而被放了气的自行车一样被边缘化了,虽然“乡音无改”,但再难找到往日的默契。正所谓“身在他乡归是客,莫叹故土不留人。”我在向西方社会传播中华经典文化和传统观念中最优秀成分的同时,对自己家门口的变化却越来越陌生。
(采编自网络;图片来自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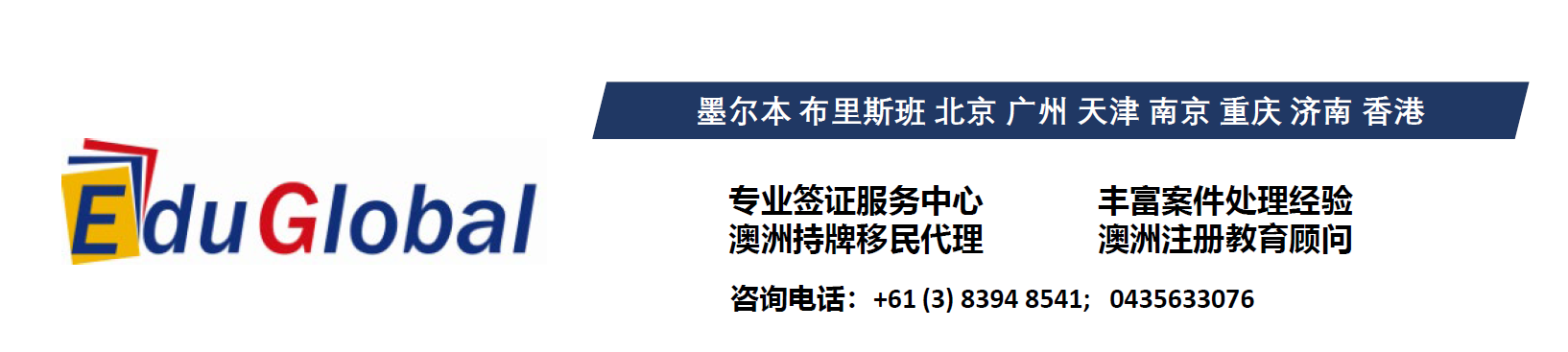 艾迪墨尔本 昆士兰 北京 广州 留学移民-22年权威经验
艾迪墨尔本 昆士兰 北京 广州 留学移民-22年权威经验



